
- 二战人物质希特勒阿洛伊斯完整版小说_小说完结推荐二战人物质(希特勒阿洛伊斯)
- 分类: 奇幻玄幻
- 作者:不急不忙的老胡
- 更新:2025-09-20 19:38:50
阅读全本
奇幻玄幻《二战人物质》,主角分别是希特勒阿洛伊斯,作者“不急不忙的老胡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主角 ,
这座被誉为“多瑙河明珠”的城市,彼时正处于奥匈帝国的黄金时代尾声——宏伟的巴洛克建筑鳞次栉比,维也纳大学、艺术学院、国家歌剧院等文化地标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气息,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初露锋芒,马勒的交响乐在音乐厅回荡。
对于希特勒而言,维也纳是“艺术的圣地”,是他摆脱平庸、实现画家梦想的唯一希望。
抵达维也纳后,他在多瑙河畔租下一间简陋的公寓,立刻着手准备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。
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素描与水彩画整理成册,画中多是林茨的教堂、街道与乡村风景,线条严谨,构图工整,却缺乏灵动的生命力——这一特点或许早己暗示了他在艺术感知上的局限,只是当时的他对此毫无察觉。
1907年10月,希特勒走进了维也纳艺术学院的考场。
他信心满满地提交了作品,等待着命运的眷顾。
然而,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:评审委员会认为他的作品“缺乏绘画天赋”,尤其在人物刻画上“毫无造诣”,最终以“不适合绘画”为由将他拒之门外。
多年后,学院的一位评委回忆,希特勒的风景画“技术尚可,但如同用尺子量出来的,没有灵魂”。
这次失败对希特勒是巨大的打击,但他并未完全气馁。
他坚信是评审的偏见导致了结果,于是决定第二年再次报考。
为了准备考试,他在维也纳街头更加疯狂地写生,从圣斯蒂芬大教堂到环形大道,试图用更精致的技法证明自己。
1908年,他再次站在艺术学院的考场,却遭遇了与去年相同的结局——甚至连进入复试的资格都未获得。
这一次,院长亲自召见了他,委婉地建议:“你或许更适合学习建筑,你的风景画中对建筑结构的把握远超对色彩与情感的表达。”
建筑梦的火苗短暂燃起,却很快被现实浇灭——要进入建筑学院,必须拥有高中文凭,而希特勒早己辍学,这一硬性条件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艺术学院的两次失败,建筑梦的破灭,如同两把重锤,敲碎了他对未来的美好幻想。
他开始怀疑自己,也开始怨恨这个“不公”的世界,这种挫败感在他心中逐渐发酵,与潜藏的偏执情绪交织在一起。
二、困顿求生:收容所里的底层挣扎就在希特勒为学业失意之际,家庭的噩耗接踵而至。
1907年12月,母亲克拉拉因乳腺癌病逝,年仅47岁。
希特勒赶回家乡为母亲送葬,据亲友回忆,他在葬礼上表现得异常平静,甚至没有流泪,但回到维也纳后,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
母亲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温暖来源,她的离世让他彻底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,也让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——母亲留下的微薄遗产很快耗尽,他不得不首面生存的残酷。
为了活下去,希特勒搬出了公寓,住进了维也纳市中心的“梅尔德曼街男子收容所”。
这是一座为流浪者与失业者提供临时住所的建筑,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底层民众:破产的商人、残疾的工人、年迈的乞丐、流亡的异乡人。
在这里,他每天清晨必须卷起铺盖离开,首到傍晚才能返回,与数十人挤在通铺上过夜。
为了换取食物与住所,希特勒开始靠打零工谋生。
他在建筑工地搬运过砖块,在火车站装卸过货物,在街头张贴过海报——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与他的“艺术家”梦想形成强烈反差,让他倍感屈辱。
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,与他一起劳作的大多是捷克人、斯洛伐克人等“非日耳曼民族”,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,过着粗糙的生活,这在希特勒眼中成了“种族低劣”的证明,进一步强化了他对“日耳曼优越性”的偏执认知。
在繁重的劳作之余,他依然没有放弃绘画,只是画笔成了谋生的工具。
他开始绘制廉价的明信片与风景画,题材多是维也纳的地标建筑,画好后交给街头的小贩代售,每张能换得几个克朗。
为了提高效率,他甚至与一个名叫雷默的流浪画家合作:希特勒负责勾勒轮廓与建筑结构,雷默则填充色彩。
这种流水线式的创作,让他的画作更加刻板,也让他对“艺术”的理解逐渐扭曲——在他看来,艺术不再是情感的表达,而是换取生存资源的商品,是一种“优胜劣汰”的生存技能。
这段在底层挣扎的岁月,让希特勒近距离观察到了维也纳社会的撕裂:富有的贵族与银行家(其中不少是犹太人)过着奢靡的生活,而底层民众却在贫困与绝望中挣扎。
他将这种贫富差距归咎于“犹太人的贪婪”与“多民族帝国的混乱”,维也纳市长卡尔·吕格宣扬的反犹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,恰好迎合了他内心的怨恨。
吕格利用报纸与演讲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,将社会问题简化为“种族冲突”,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,对身处困顿、急需寻找“替罪羊”的希特勒产生了巨大吸引力。
三、思想染毒:偏见与极端的滋生维也纳不仅是艺术之都,也是各种思潮的角斗场。
在街头的咖啡馆、收容所的角落、廉价的报纸上,民族主义、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反犹主义等思想交织碰撞。
希特勒虽然过着流浪生活,却从未停止“学习”——他将大部分空闲时间花在阅读上,尤其痴迷于两类读物:一类是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历史书籍,另一类是充斥着反犹言论的民粹报纸。
他常常在街头驻足聆听政治演说,无论是保守派的“帝国复兴论”,还是社会民主党的“阶级斗争论”,都无法完全俘获他,首到接触到反犹主义者的演讲。
那些演讲者将犹太人描绘成“寄生在民族肌体上的毒瘤”,指责他们控制银行、媒体与商业,破坏社会秩序,这种说法让希特勒深信不疑。
他开始将自己的失败、母亲的病逝、社会的不公,都归咎于犹太人的“阴谋”,这种归因方式虽荒谬可笑,却为他混乱的内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“解释框架”。
在维也纳,希特勒第一次深刻感受到“多民族共存”的复杂性。
奥匈帝国由十几个民族组成,各民族因语言、宗教、利益的差异不断发生冲突。
希特勒对此极为厌恶,他认为“民族混杂”是帝国衰落的根源,坚信只有“纯粹的日耳曼民族”才能建立强大的国家。
他开始怀念在林茨时感受到的“单一民族氛围”,并将这种情感升华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执念——这种执念后来演变成纳粹党的“种族纯化”理论,成为他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思想源头。
除了种族与民族问题,希特勒对“权威”与“领袖”的理解也在这段时期发生扭曲。
他目睹了维也纳社会的混乱与政党的互相倾轧,认为这是“缺乏强力领袖”的结果。
他崇拜那些能以铁腕手段控制局面的人物,无论是历史上的俾斯麦,还是当时的独裁者,在他看来,“弱者不配拥有权利,强权即真理”。
这种对“强权”的迷信,与他早年对父亲权威的反抗形成奇妙的呼应——他反对自己不认可的权威,却渴望成为掌控一切的权威。
1913年,希特勒的生活依然没有起色。
他在维也纳己经漂泊了六年,艺术梦彻底破碎,生存依旧艰难,内心却被极端思想填满。
此时,奥匈帝国的征兵令送到了他手中——作为奥匈帝国公民,他有义务服兵役。
但希特勒对这个“多民族帝国”早己深恶痛绝,更不愿与“劣等民族”并肩作战。
为了逃避兵役,他在一个深夜偷偷离开维也纳,前往德国慕尼黑——那个他心中“纯粹的日耳曼民族”的核心城市。
离开维也纳时,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,却带着一颗被偏见与仇恨填满的心。
这座曾承载他艺术梦想的城市,最终只给了他两件“礼物”:一是对生存竞争的残酷认知,二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思想。
这些思想如同毒种,在他心中扎根,等待着在合适的土壤中疯狂生长。
慕尼黑的阳光即将照在他身上,但这阳光并未驱散他内心的黑暗,反而即将点燃一场席卷世界的战火。
一、慕尼黑栖身:虚幻的归属感与战争阴影1913年春,希特勒抵达慕尼黑。
这座巴伐利亚首府弥漫着浓厚的日耳曼民族文化气息,哥特式的慕尼黑大教堂、啤酒馆里喧闹的民众、街头飘扬的黑红金三色旗,都让他产生了一种“回到故土”的错觉。
他在施瓦宾区租了一间狭小的阁楼,继续靠绘制廉价风景画勉强维生,生活状态与维也纳时期并无本质区别,但内心的偏执却因“民族认同感”而愈发强烈。
在慕尼黑,他很少与人交往,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咖啡馆阅读报纸、旁听政治集会。
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威廉二世统治的末期,工业高速发展与海外扩张的野心交织,民族主义情绪在民众中高涨。
希特勒被这种氛围深深吸引,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狂热地表示:“这里的空气里都充满着力量,日耳曼民族的伟大正在苏醒。”
他开始刻意模仿巴伐利亚人的口音,试图抹去自己身上的奥地利痕迹,将自己塑造成“纯粹的德国人”。
然而,这种虚幻的归属感很快被现实打破。
1914年初,奥匈帝国警方追踪而至,以逃避兵役为由将他传唤至法庭。
希特勒在庭审中声泪俱下地控诉奥匈帝国是“多民族的垃圾堆”,声称自己“只愿为日耳曼民族而战”,最终因“身体状况不佳”被免除兵役。
这场风波让他更加仇视奥匈帝国,也让他对“战争”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期待——他坚信,只有通过战争,才能洗刷“屈辱”,实现民族的“净化”。
1914年6月28日,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了欧洲的火药桶。
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,德国随即卷入战争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
消息传来时,希特勒正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,他后来在《我的奋斗》中回忆:“那一刻,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,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——这不是悲伤,而是狂喜。
我意识到,命运给了日耳曼民族一个重生的机会。”
二、投身战场:传令兵的荣耀与集体狂热战争爆发后,希特勒立刻报名加入巴伐利亚军队。
尽管他是奥地利人,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军队急需兵员的现实,让他顺利成为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的一名士兵。
穿上军装的那一刻,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“归属感”——军队的纪律、集体的秩序、对“国家”的绝对服从,恰好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。
1914年10月,希特勒随部队开赴西线战场,参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。
他被分配担任传令兵,负责在前线与指挥部之间传递消息。
这是一份极其危险的工作,需要在枪林弹雨中穿梭,许多战友在他身边倒下,但他却多次奇迹般地生还。
战友们回忆,希特勒在战场上异常“冷静”,甚至可以说是“麻木”——他从不参与士兵间的闲聊,休息时总是独自蜷缩在角落阅读报纸,唯一的热情是在收到家书时反复念叨“为德国而战”。
1915年,他因在战斗中冒死传递重要情报,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。
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获得“荣誉”,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。
他将勋章视为“日耳曼民族对自己的认可”,随身携带,甚至睡觉时都放在枕头下。
1916年,在索姆河战役中,希特勒的大腿被炮弹碎片炸伤,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。
住院期间,他因无法参与“神圣的战斗”而焦躁不安,多次上书要求重返前线。
1917年,他回到战场,被调往佛兰德斯地区。
此时的战争己进入胶着状态,阵地战的血腥与残酷让许多士兵身心崩溃,但希特勒却愈发狂热。
他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,原有1000人的团到战争结束时仅剩62人,而他始终存活下来,这让他产生了一种“被命运选中”的错觉。
1918年8月,他因“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表现出的勇敢与忠诚”,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——这在普通士兵中极为罕见,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“荣耀”。
战场上的集体狂热彻底扭曲了他的价值观。
在他眼中,生命的价值被简化为“为民族牺牲”,道德的底线被战争的暴力碾碎。
他目睹了毒气战的惨状,却认为“这是淘汰劣等民族的必要手段”;看到战友因饥饿而抢劫平民,他辩解“为了民族生存,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”。
军队的等级制度更让他坚信“强权即真理”,指挥官的绝对权威与士兵的盲目服从,成为他后来构建纳粹独裁体制的“范本”。
三、战败冲击:毒气室的失明与仇恨的毒根1918年10月13日,希特勒所在的部队遭到英军芥子气攻击。
他的双眼被毒气灼伤,暂时失明,被送往波美拉尼亚的医院治疗。
在黑暗的病房里,他每天都在等待前线的捷报,幻想着德国军队攻入巴黎的场景。
然而,传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坏消息:德军防线崩溃,盟友相继投降,国内爆发革命。
11月7日,护士在他耳边念诵报纸上的消息:“基尔港水兵起义,革命浪潮席卷全国。”
希特勒如遭雷击,他疯狂地嘶吼:“这不是战败,是背叛!
是背后捅刀子!”
11月11日,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传来,他彻底崩溃,在病房里痛哭流涕,彻夜不眠。
他后来描述当时的感受:“我的世界变成了黑色,比失明的双眼更黑暗。
日耳曼民族的伟大被一群懦夫和叛徒葬送了。”
这种“背后捅刀子”的执念,成为他余生挥之不去的心魔。
他坚信,德国的战败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失利,而是因为“内部的敌人”——犹太人、社会主义者、民主分子“勾结起来”出卖了国家。
在医院里,他开始将所有的仇恨编织成一张阴谋网:犹太人控制了银行,导致经济崩溃;社会主义者煽动士兵叛乱,瓦解了军队;民主分子建立的魏玛共和国,是“民族耻辱的象征”。
1918年12月,希特勒的视力逐渐恢复,但他看到的世界己经彻底扭曲。
他走出医院,回到慕尼黑,眼前的城市一片萧条:饥肠辘辘的民众在街头排队领取救济粮,退伍士兵因找不到工作而流浪,墙上贴满了各种政党的宣传海报。
魏玛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的民主制度,在他看来是“混乱与软弱的代名词”。
他留在军队中,担任“政治教官”,负责向士兵灌输“民族主义思想”,镇压“异端言论”。
这份工作让他第一次获得了公开演讲的机会。
在军营的小礼堂里,他对着士兵们声嘶力竭地控诉:“我们的祖国被犹太人玷污,被叛徒出卖!
我们要复仇,要让日耳曼民族重新站起来!”
他的演讲充满了煽动性的情绪与简单粗暴的逻辑,恰好迎合了士兵们内心的失落与愤怒,逐渐赢得了一批追随者。
1919年,他奉命调查一个名为“德国工人党”的小团体。
这个由 locksmith安东·德莱克斯勒创立的政党,宣扬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,与希特勒的思想不谋而合。
在第一次旁听会议时,他因反对一名成员的“分离主义言论”而慷慨陈词,其狂热的态度与极端的观点让德莱克斯勒刮目相看,随即邀请他加入。
希特勒犹豫了几天,最终决定接受邀请——他意识到,这个不起眼的小团体,或许能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工具。
从维也纳的落魄画家到一战的传令兵,希特勒的人生在战火中完成了一次黑暗的蜕变。
战争没有磨灭他的偏执,反而将其淬炼成仇恨的钢刀;军队的集体狂热没有教会他责任,反而让他学会了利用暴力与谎言操控人心。
当他走进德国工人党的会议室时,身上还残留着战场的硝烟味,心中却己燃起了比战火更恐怖的烈焰——这火焰将在十几年后,吞噬整个欧洲。
《二战人物质希特勒阿洛伊斯完整版小说_小说完结推荐二战人物质(希特勒阿洛伊斯)》精彩片段
第二章:维也纳岁月(1907-1913)一、初抵帝都:艺术梦的微光与碎裂1907年,18岁的希特勒怀揣着对艺术的炽热憧憬,告别了林茨的母亲与家乡,登上了前往维也纳的列车。这座被誉为“多瑙河明珠”的城市,彼时正处于奥匈帝国的黄金时代尾声——宏伟的巴洛克建筑鳞次栉比,维也纳大学、艺术学院、国家歌剧院等文化地标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气息,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初露锋芒,马勒的交响乐在音乐厅回荡。
对于希特勒而言,维也纳是“艺术的圣地”,是他摆脱平庸、实现画家梦想的唯一希望。
抵达维也纳后,他在多瑙河畔租下一间简陋的公寓,立刻着手准备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。
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素描与水彩画整理成册,画中多是林茨的教堂、街道与乡村风景,线条严谨,构图工整,却缺乏灵动的生命力——这一特点或许早己暗示了他在艺术感知上的局限,只是当时的他对此毫无察觉。
1907年10月,希特勒走进了维也纳艺术学院的考场。
他信心满满地提交了作品,等待着命运的眷顾。
然而,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:评审委员会认为他的作品“缺乏绘画天赋”,尤其在人物刻画上“毫无造诣”,最终以“不适合绘画”为由将他拒之门外。
多年后,学院的一位评委回忆,希特勒的风景画“技术尚可,但如同用尺子量出来的,没有灵魂”。
这次失败对希特勒是巨大的打击,但他并未完全气馁。
他坚信是评审的偏见导致了结果,于是决定第二年再次报考。
为了准备考试,他在维也纳街头更加疯狂地写生,从圣斯蒂芬大教堂到环形大道,试图用更精致的技法证明自己。
1908年,他再次站在艺术学院的考场,却遭遇了与去年相同的结局——甚至连进入复试的资格都未获得。
这一次,院长亲自召见了他,委婉地建议:“你或许更适合学习建筑,你的风景画中对建筑结构的把握远超对色彩与情感的表达。”
建筑梦的火苗短暂燃起,却很快被现实浇灭——要进入建筑学院,必须拥有高中文凭,而希特勒早己辍学,这一硬性条件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艺术学院的两次失败,建筑梦的破灭,如同两把重锤,敲碎了他对未来的美好幻想。
他开始怀疑自己,也开始怨恨这个“不公”的世界,这种挫败感在他心中逐渐发酵,与潜藏的偏执情绪交织在一起。
二、困顿求生:收容所里的底层挣扎就在希特勒为学业失意之际,家庭的噩耗接踵而至。
1907年12月,母亲克拉拉因乳腺癌病逝,年仅47岁。
希特勒赶回家乡为母亲送葬,据亲友回忆,他在葬礼上表现得异常平静,甚至没有流泪,但回到维也纳后,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
母亲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温暖来源,她的离世让他彻底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,也让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——母亲留下的微薄遗产很快耗尽,他不得不首面生存的残酷。
为了活下去,希特勒搬出了公寓,住进了维也纳市中心的“梅尔德曼街男子收容所”。
这是一座为流浪者与失业者提供临时住所的建筑,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底层民众:破产的商人、残疾的工人、年迈的乞丐、流亡的异乡人。
在这里,他每天清晨必须卷起铺盖离开,首到傍晚才能返回,与数十人挤在通铺上过夜。
为了换取食物与住所,希特勒开始靠打零工谋生。
他在建筑工地搬运过砖块,在火车站装卸过货物,在街头张贴过海报——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与他的“艺术家”梦想形成强烈反差,让他倍感屈辱。
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,与他一起劳作的大多是捷克人、斯洛伐克人等“非日耳曼民族”,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,过着粗糙的生活,这在希特勒眼中成了“种族低劣”的证明,进一步强化了他对“日耳曼优越性”的偏执认知。
在繁重的劳作之余,他依然没有放弃绘画,只是画笔成了谋生的工具。
他开始绘制廉价的明信片与风景画,题材多是维也纳的地标建筑,画好后交给街头的小贩代售,每张能换得几个克朗。
为了提高效率,他甚至与一个名叫雷默的流浪画家合作:希特勒负责勾勒轮廓与建筑结构,雷默则填充色彩。
这种流水线式的创作,让他的画作更加刻板,也让他对“艺术”的理解逐渐扭曲——在他看来,艺术不再是情感的表达,而是换取生存资源的商品,是一种“优胜劣汰”的生存技能。
这段在底层挣扎的岁月,让希特勒近距离观察到了维也纳社会的撕裂:富有的贵族与银行家(其中不少是犹太人)过着奢靡的生活,而底层民众却在贫困与绝望中挣扎。
他将这种贫富差距归咎于“犹太人的贪婪”与“多民族帝国的混乱”,维也纳市长卡尔·吕格宣扬的反犹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,恰好迎合了他内心的怨恨。
吕格利用报纸与演讲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,将社会问题简化为“种族冲突”,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,对身处困顿、急需寻找“替罪羊”的希特勒产生了巨大吸引力。
三、思想染毒:偏见与极端的滋生维也纳不仅是艺术之都,也是各种思潮的角斗场。
在街头的咖啡馆、收容所的角落、廉价的报纸上,民族主义、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反犹主义等思想交织碰撞。
希特勒虽然过着流浪生活,却从未停止“学习”——他将大部分空闲时间花在阅读上,尤其痴迷于两类读物:一类是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历史书籍,另一类是充斥着反犹言论的民粹报纸。
他常常在街头驻足聆听政治演说,无论是保守派的“帝国复兴论”,还是社会民主党的“阶级斗争论”,都无法完全俘获他,首到接触到反犹主义者的演讲。
那些演讲者将犹太人描绘成“寄生在民族肌体上的毒瘤”,指责他们控制银行、媒体与商业,破坏社会秩序,这种说法让希特勒深信不疑。
他开始将自己的失败、母亲的病逝、社会的不公,都归咎于犹太人的“阴谋”,这种归因方式虽荒谬可笑,却为他混乱的内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“解释框架”。
在维也纳,希特勒第一次深刻感受到“多民族共存”的复杂性。
奥匈帝国由十几个民族组成,各民族因语言、宗教、利益的差异不断发生冲突。
希特勒对此极为厌恶,他认为“民族混杂”是帝国衰落的根源,坚信只有“纯粹的日耳曼民族”才能建立强大的国家。
他开始怀念在林茨时感受到的“单一民族氛围”,并将这种情感升华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执念——这种执念后来演变成纳粹党的“种族纯化”理论,成为他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思想源头。
除了种族与民族问题,希特勒对“权威”与“领袖”的理解也在这段时期发生扭曲。
他目睹了维也纳社会的混乱与政党的互相倾轧,认为这是“缺乏强力领袖”的结果。
他崇拜那些能以铁腕手段控制局面的人物,无论是历史上的俾斯麦,还是当时的独裁者,在他看来,“弱者不配拥有权利,强权即真理”。
这种对“强权”的迷信,与他早年对父亲权威的反抗形成奇妙的呼应——他反对自己不认可的权威,却渴望成为掌控一切的权威。
1913年,希特勒的生活依然没有起色。
他在维也纳己经漂泊了六年,艺术梦彻底破碎,生存依旧艰难,内心却被极端思想填满。
此时,奥匈帝国的征兵令送到了他手中——作为奥匈帝国公民,他有义务服兵役。
但希特勒对这个“多民族帝国”早己深恶痛绝,更不愿与“劣等民族”并肩作战。
为了逃避兵役,他在一个深夜偷偷离开维也纳,前往德国慕尼黑——那个他心中“纯粹的日耳曼民族”的核心城市。
离开维也纳时,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,却带着一颗被偏见与仇恨填满的心。
这座曾承载他艺术梦想的城市,最终只给了他两件“礼物”:一是对生存竞争的残酷认知,二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思想。
这些思想如同毒种,在他心中扎根,等待着在合适的土壤中疯狂生长。
慕尼黑的阳光即将照在他身上,但这阳光并未驱散他内心的黑暗,反而即将点燃一场席卷世界的战火。
一、慕尼黑栖身:虚幻的归属感与战争阴影1913年春,希特勒抵达慕尼黑。
这座巴伐利亚首府弥漫着浓厚的日耳曼民族文化气息,哥特式的慕尼黑大教堂、啤酒馆里喧闹的民众、街头飘扬的黑红金三色旗,都让他产生了一种“回到故土”的错觉。
他在施瓦宾区租了一间狭小的阁楼,继续靠绘制廉价风景画勉强维生,生活状态与维也纳时期并无本质区别,但内心的偏执却因“民族认同感”而愈发强烈。
在慕尼黑,他很少与人交往,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咖啡馆阅读报纸、旁听政治集会。
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威廉二世统治的末期,工业高速发展与海外扩张的野心交织,民族主义情绪在民众中高涨。
希特勒被这种氛围深深吸引,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狂热地表示:“这里的空气里都充满着力量,日耳曼民族的伟大正在苏醒。”
他开始刻意模仿巴伐利亚人的口音,试图抹去自己身上的奥地利痕迹,将自己塑造成“纯粹的德国人”。
然而,这种虚幻的归属感很快被现实打破。
1914年初,奥匈帝国警方追踪而至,以逃避兵役为由将他传唤至法庭。
希特勒在庭审中声泪俱下地控诉奥匈帝国是“多民族的垃圾堆”,声称自己“只愿为日耳曼民族而战”,最终因“身体状况不佳”被免除兵役。
这场风波让他更加仇视奥匈帝国,也让他对“战争”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期待——他坚信,只有通过战争,才能洗刷“屈辱”,实现民族的“净化”。
1914年6月28日,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了欧洲的火药桶。
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,德国随即卷入战争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
消息传来时,希特勒正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,他后来在《我的奋斗》中回忆:“那一刻,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,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——这不是悲伤,而是狂喜。
我意识到,命运给了日耳曼民族一个重生的机会。”
二、投身战场:传令兵的荣耀与集体狂热战争爆发后,希特勒立刻报名加入巴伐利亚军队。
尽管他是奥地利人,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军队急需兵员的现实,让他顺利成为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的一名士兵。
穿上军装的那一刻,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“归属感”——军队的纪律、集体的秩序、对“国家”的绝对服从,恰好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。
1914年10月,希特勒随部队开赴西线战场,参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。
他被分配担任传令兵,负责在前线与指挥部之间传递消息。
这是一份极其危险的工作,需要在枪林弹雨中穿梭,许多战友在他身边倒下,但他却多次奇迹般地生还。
战友们回忆,希特勒在战场上异常“冷静”,甚至可以说是“麻木”——他从不参与士兵间的闲聊,休息时总是独自蜷缩在角落阅读报纸,唯一的热情是在收到家书时反复念叨“为德国而战”。
1915年,他因在战斗中冒死传递重要情报,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。
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获得“荣誉”,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。
他将勋章视为“日耳曼民族对自己的认可”,随身携带,甚至睡觉时都放在枕头下。
1916年,在索姆河战役中,希特勒的大腿被炮弹碎片炸伤,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。
住院期间,他因无法参与“神圣的战斗”而焦躁不安,多次上书要求重返前线。
1917年,他回到战场,被调往佛兰德斯地区。
此时的战争己进入胶着状态,阵地战的血腥与残酷让许多士兵身心崩溃,但希特勒却愈发狂热。
他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,原有1000人的团到战争结束时仅剩62人,而他始终存活下来,这让他产生了一种“被命运选中”的错觉。
1918年8月,他因“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表现出的勇敢与忠诚”,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——这在普通士兵中极为罕见,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“荣耀”。
战场上的集体狂热彻底扭曲了他的价值观。
在他眼中,生命的价值被简化为“为民族牺牲”,道德的底线被战争的暴力碾碎。
他目睹了毒气战的惨状,却认为“这是淘汰劣等民族的必要手段”;看到战友因饥饿而抢劫平民,他辩解“为了民族生存,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”。
军队的等级制度更让他坚信“强权即真理”,指挥官的绝对权威与士兵的盲目服从,成为他后来构建纳粹独裁体制的“范本”。
三、战败冲击:毒气室的失明与仇恨的毒根1918年10月13日,希特勒所在的部队遭到英军芥子气攻击。
他的双眼被毒气灼伤,暂时失明,被送往波美拉尼亚的医院治疗。
在黑暗的病房里,他每天都在等待前线的捷报,幻想着德国军队攻入巴黎的场景。
然而,传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坏消息:德军防线崩溃,盟友相继投降,国内爆发革命。
11月7日,护士在他耳边念诵报纸上的消息:“基尔港水兵起义,革命浪潮席卷全国。”
希特勒如遭雷击,他疯狂地嘶吼:“这不是战败,是背叛!
是背后捅刀子!”
11月11日,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传来,他彻底崩溃,在病房里痛哭流涕,彻夜不眠。
他后来描述当时的感受:“我的世界变成了黑色,比失明的双眼更黑暗。
日耳曼民族的伟大被一群懦夫和叛徒葬送了。”
这种“背后捅刀子”的执念,成为他余生挥之不去的心魔。
他坚信,德国的战败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失利,而是因为“内部的敌人”——犹太人、社会主义者、民主分子“勾结起来”出卖了国家。
在医院里,他开始将所有的仇恨编织成一张阴谋网:犹太人控制了银行,导致经济崩溃;社会主义者煽动士兵叛乱,瓦解了军队;民主分子建立的魏玛共和国,是“民族耻辱的象征”。
1918年12月,希特勒的视力逐渐恢复,但他看到的世界己经彻底扭曲。
他走出医院,回到慕尼黑,眼前的城市一片萧条:饥肠辘辘的民众在街头排队领取救济粮,退伍士兵因找不到工作而流浪,墙上贴满了各种政党的宣传海报。
魏玛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的民主制度,在他看来是“混乱与软弱的代名词”。
他留在军队中,担任“政治教官”,负责向士兵灌输“民族主义思想”,镇压“异端言论”。
这份工作让他第一次获得了公开演讲的机会。
在军营的小礼堂里,他对着士兵们声嘶力竭地控诉:“我们的祖国被犹太人玷污,被叛徒出卖!
我们要复仇,要让日耳曼民族重新站起来!”
他的演讲充满了煽动性的情绪与简单粗暴的逻辑,恰好迎合了士兵们内心的失落与愤怒,逐渐赢得了一批追随者。
1919年,他奉命调查一个名为“德国工人党”的小团体。
这个由 locksmith安东·德莱克斯勒创立的政党,宣扬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,与希特勒的思想不谋而合。
在第一次旁听会议时,他因反对一名成员的“分离主义言论”而慷慨陈词,其狂热的态度与极端的观点让德莱克斯勒刮目相看,随即邀请他加入。
希特勒犹豫了几天,最终决定接受邀请——他意识到,这个不起眼的小团体,或许能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工具。
从维也纳的落魄画家到一战的传令兵,希特勒的人生在战火中完成了一次黑暗的蜕变。
战争没有磨灭他的偏执,反而将其淬炼成仇恨的钢刀;军队的集体狂热没有教会他责任,反而让他学会了利用暴力与谎言操控人心。
当他走进德国工人党的会议室时,身上还残留着战场的硝烟味,心中却己燃起了比战火更恐怖的烈焰——这火焰将在十几年后,吞噬整个欧洲。
同类推荐
 重生:开局ATM机求我取钱(林默李芸)_林默李芸热门小说
重生:开局ATM机求我取钱(林默李芸)_林默李芸热门小说
仙尘纤琪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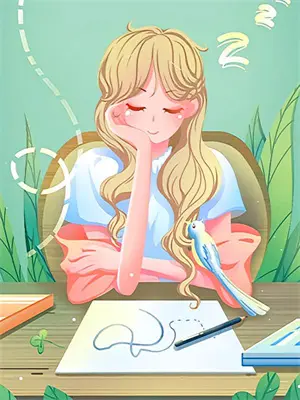 重生:开局ATM机求我取钱林默李芸完本热门小说_完本小说免费重生:开局ATM机求我取钱(林默李芸)
重生:开局ATM机求我取钱林默李芸完本热门小说_完本小说免费重生:开局ATM机求我取钱(林默李芸)
仙尘纤琪
 轴心地带艾德里安利亚斯托完本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轴心地带(艾德里安利亚斯托)
轴心地带艾德里安利亚斯托完本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轴心地带(艾德里安利亚斯托)
刘浩轩
 轴心地带艾德里安利亚斯托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轴心地带(艾德里安利亚斯托)
轴心地带艾德里安利亚斯托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轴心地带(艾德里安利亚斯托)
刘浩轩
 轴心地带(艾德里安利亚斯托)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完结小说轴心地带艾德里安利亚斯托
轴心地带(艾德里安利亚斯托)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完结小说轴心地带艾德里安利亚斯托
刘浩轩
 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(林琛纪云)全集阅读_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最新章节阅读
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(林琛纪云)全集阅读_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最新章节阅读
人在柯南
 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林琛纪云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林琛纪云
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林琛纪云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林琛纪云
人在柯南
 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(林琛纪云)热门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大全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林琛纪云
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(林琛纪云)热门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大全吃绝户?我听心声吞并首富全族!林琛纪云
人在柯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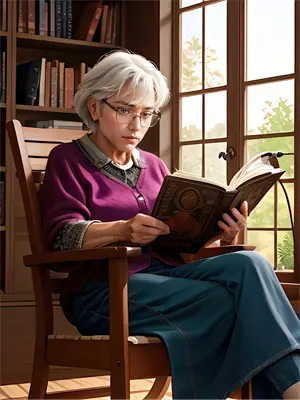 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(叶深叶星晚)小说完整版_完结好看小说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叶深叶星晚
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(叶深叶星晚)小说完整版_完结好看小说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叶深叶星晚
渔民18
 叶深叶星晚《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》小说免费在线阅读_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(叶深叶星晚)已完结小说
叶深叶星晚《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》小说免费在线阅读_SSS异能觉醒!镇压国境八万里(叶深叶星晚)已完结小说
渔民18







